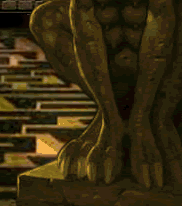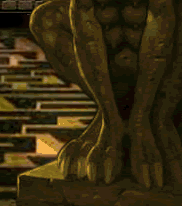宗教裁判所的运作
至于神圣法庭的运作方式,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正如我们在
神圣法庭的人员设置中便能体会到的那样,神圣法庭对罗马法开创的西方法学
传统有所继承甚至有所发展,它的许多操作同当时世俗法庭的常规是衔接的,
我们完全可以在西方法律史的读物中了解和熟悉此类运作--它们的不少部分甚
至活化石般地残留在当代西方的司法制度中。
神圣法庭特色的是无孔不入的告密制度和触及灵魂的肉体刑罚,就是它们
规范和威慑着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就是它们铸就了宗教裁判所永远洗刷
不了的臭名。也许,告密制度在任何法律体制下都有其地位,但由于思想的隐
秘性,神圣法庭将它发展到了极致;在人类刑事实践从肉体惩罚转为心灵训导
--法国大思想家福柯对此有专门研究--之前,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有长期使用
身体刑的记录,但神圣法庭由于其审判对象的特殊性,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公元前十六世纪,陪葬在古埃及坟墓中的著名文献《死者书》便把间谍工
作描绘为危及灵魂的罪行;时到今日,间谍还是这个时代以及下个时代规模最
大的行业之一,而日常道德仍然谴责任何刺探他人秘密的行为。但是,神圣法
庭却在中世纪欧洲动员起全民规模的告密运动——这可以使我们联想起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此间,侦探和出卖他人内心的信仰秘密成为了每个欧洲人
的义务,而且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生存和生活的必要条件。
基督教的告解制度---基督教的原罪理论特别是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的决
议要求信徒以痛悔、告罪和补赎的方式来取悦上帝和获得上帝的宽恕--为这场
告密运动提供了现成而有效的工具;痛悔可以彻底摧毁信徒的自我肯定,告罪
为告密提供了直接的渠道,补赎构成了告密的激励机制。秘密警察的本性决定
了宗教裁判员必须像老鼠一样在阴暗中活动,但是为了发动群众,他们有时也
不惜抛头露面。一般情况下如在神圣法庭非常设地区,宗教裁判员每到一地,
便在当地主教举行欢迎仪式上上布道,这种布道实际上是告密运动的一次誓师。
宗教裁判员开诚布公地说明他的使命,要求异端知情者在六十天内向他汇报异
端的情况--主要就是利用告罪忏悔的机会,知情不报者和不合作者将开除出教,
响应号召者将获得为期三年的免罪券。对于异端,宗教裁判员也表示不抛弃他
们,但要求他们立刻在半到一个月的"仁慈期"里主动投案,并供出同案犯以显
示诚意。宗教裁判员还在布道中说明异端的标志、特点和伪装,于是这次布道
还带有职业培训味道。
告密在神圣法庭的常设地区则周期为日常功课。在西班牙--那里是神圣法
庭的一个重灾区,复活节前夕是个鬼门关,人们必须时刻警惕着门外的动静,
每一次的敲门都足以让他们胆战心惊,因为告密风暴此刻正汹涌澎湃。西班牙
神圣法庭特别规定,每个教徒在大斋期--即复活节前的四十天--中的六天时间
内必须密告异端和异端嫌疑,拒绝合作者或错过期限者的信徒不得参加圣餐礼,
并注定受到革除教门甚至死罪的惩处。就这样,恐怖的氛围摧毁了社会成员的
安全感,而恐慌和猜疑的心理推动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告密风潮,于是每个人都
可能由于邻居的道听途说甚至胡说八道而半夜三更被从床上拖出来,投进污秽
阴暗的地牢。--宗教裁判所对拘犯一直有数量上的追求,它可以借拖延侦查期
敛财,因为嫌犯坐牢的费用是自理的,就像当代某些国家的死刑犯得自己承担
子弹费那样。
任何动机的推究都带有心理还原的色彩;对于中世纪那场轰轰烈烈的告密
运动,我们并不能将参与其中者完全地归类为狭隘利己主义分子。果然,告密
活动必然最大程度地暴露人类的自私本性--这恐怕是人永远进化不了的心灵尾
巴;在中世纪,告密者中的许多难免是为自私本性所驱逐而买卖他人的思想隐
私以赢利,利欲之徒由于贪婪之心的不可遏制——觊觎他人的财产甚至可怜只
为了几文下酒钱,游手好闲者以之为里比多发泄的渠道,官运不济者恐怕难以
拒绝这种升迁机会的诱惑,胆小怕事者也许可能出于自救自保之下的无可奈何,
高尚如复仇之类则以之不露痕迹地借刀杀人。但是,正如当代政治学研究所表
明的,权力的有效维持不仅由于其体制自身的强制力量而且因为其意识形态的
纵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之外,展
开了对资本主义文化体制的剖析和抨击。毫无疑问,基督教正统的意识形态工
程虽然在中世纪后期受到了异端的挑战和冲击,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千年
基业的崩溃需要时间的积累,结果便是即使卑鄙如宗教裁判所的告密动员的活
动也能自然而然地获得正义、神圣和集体之类理念的辩护。手段的卑鄙经常为
目的的高尚所平衡;正在基督教正统意识形态的欺骗和诱导下,中世纪的许多
密告者在刺探或出卖他人时确实真诚地认为自己只是为上帝的事业尽点责,甚
至是为了拯救异端——免得他们死后永坠地狱。多么可爱的利他主义啊!结果
则是火刑柱上的烟尘竟弥漫了数百年之久。
为了告密活动的深入和持续,神圣法庭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其中的根
本原则便是"宁可错杀十万,不可漏网一人"。在神圣法庭上,被告和控告人
及证人互不见面,被告不得知晓告密者的姓名和身份;而当时世俗法庭从十四
世纪起便规定,被告有权力面对证人或证词,原告控告有误则得接受惩罚并赔
偿被告的损失。神圣法庭的告密者和被告密者不受职业和地位的限制,甚至连
在世俗法庭上不具法律地位的刑事犯都可充当控告人和见证人;曾经有规定说
只有年满十四岁的少年和年满十二岁的少女才能成为控告人或被告人,但实际
执行的情况是令人沮丧的。异端一旦受控告——控告有两人作证便成立,即使
表示悔改,也必须出卖他的同谋、朋友以及其他疑犯,任何的推诿迟疑都可视
为忏悔不彻底的表现。告密者不得撤回证词,否则以异端同谋犯论处。真是专
业水平!中世纪的思想警察们充分地估计到了思想的隐秘性,因而将其情治系
统造就得如此细密和严谨以不放过任何捕捉异端的可能。
当人们以"黑暗"来命名欧洲的中世纪时,其意味主要落实为人类精神在
那个时代的萎缩和委琐;但是,责怪那个时代的人们真是一种残酷,因为正如
我们所见到的,他们所面对的情治系统强大和严密得足以让任何良心发颤。盘
点一下宗教裁判所的累累战果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一开始的受害者是可能货
真价实的异端,然后是异端的嫌疑,再以后便是莫须有了;宗教裁判员总是对
形势持悲观的看法,在他们的眼里,异端的存在并非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而是
发现或者没有发现的问题--平心而论,也确实很难保证一个并非白痴的人没有
一点的见解独特或一时的心灵发挥。也正因为如此,在全社会的揭发和自我揭
发之下,中世纪欧洲社会陷入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并最大程度上遏制精神的自由
和创造;如果无所不在的监控和生死难卜的惩罚本身便是令人发指的恐怖,那
么思想的所谓罪行--在中国即"腹诽罪"--因其界限的模糊及定罪的随意而平
添更多的恐怖特别是心理上的恐慌。
关于这次告密运动的牺牲者,最保守的统计也显示有几百万之多;联想一
下欧洲当时的总人口数,如在十四世纪中期黑死病流行前欧洲人口只徘徊在六
千万至八千万之间--黑死病随后就消灭了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应该震
惊于宗教裁判所的这一辉煌战果。一个统计数字显示,从十五末世纪到十九世
纪初,宗教裁判所以传统异端罪便正式处罚了三十四万名被告,共有三万余人
被押上火刑柱。女巫也是宗教裁判所重点打击的一种特殊异端,她们牺牲惨重,
其受迫害总量的估算起码几十万甚至高达几百万,有些地区一年内受审判的女
巫数竟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再举一个宗教裁判员的个案;托尔克马达,西
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他在十七年的任职期间,有一万余人因异端罪
被他判处火刑,另有近十万人被判处其他刑罚,其中还不包括对死者或缺席者
所作的近七千件象征性火刑判决。
自然,出于高尚或不高尚的考虑,异端嫌疑犯即使被捕,面对宗教裁判所
精致而科学的审讯手段,也并非个个竹筒倒豆子,大包大揽地接受对他们内心
世界的种种指控。在这种情况下,宗教裁判所的另一条撒手锏立刻脱手而出,
这就是其触及灵魂的肉刑制度。
虽然神圣法庭的辩护士们在肉刑使用的使用问题上总是闪烁其辞,但是我
们清楚地发现,宗教裁判所不仅存在大量使用肉刑的事实,而且精神审判的特
性也决定了它必然依赖这种血腥的手段。首先,由于思想区别于实在的特异性,
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必然特别地重视口供。在中世纪,除了思想家异端可能拥有
事实的证据如书籍或手稿外,宗教裁判所对其他被告的控告只能基于他人的描
述和自己的承认之上;例如神圣法庭一开始的逮捕程序——这实际上是对异端
的定罪过程,宗教裁判员凭借告发者的口供便对异端嫌疑犯立案,然后传讯可
能的证人、收集嫌犯的背景材料并与其他宗教裁判所交换该嫌犯的信息--幸亏
当时尚没有计算机联网,这些口供材料只要经鉴定人认定后便可实施逮捕。其
次,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嫌犯一经逮捕,他的异端罪名已经铁板钉钉不容争辩了;
神圣法庭对它的被告一律作有罪推断,它的兴趣在于如何让异端分子痛快淋漓
地悔悟而非纠缠于异端嫌犯有没有罪的问题--任何有利于被告的证词都可由于
包庇的怀疑而遭到拒绝,宗教裁判所怎么可能错误呢?另外,宗教裁判所将它
自己同一个神圣的目的相联络,这就决定宗教裁判员能够毫无顾忌地动员一切
可能的手段;事实上,为了维护"神圣"的正统教会,宗教裁判所不惜任何代
价包括欺骗和威胁在内,刑讯逼供在其中也只不过是方便法门之一而已。
应该说,宗教裁判所一开始在肉刑使用问题上有过犹豫和不安,毕竟肉刑
制度的残酷和暴虐离教会所标榜的仁慈和人道太远了。但是,1252年,教皇英
诺诚四世在现实的利益和抽象的良心之间作了一番抉择后,还是咬咬牙在其著
名的《论连根拔除》通谕中,命令宗教裁判员对异端嫌疑犯用刑,"用暴力强
迫一切被捕的异端者",迫使他们像窃贼揭发其共犯那样供认他们罪行,只是
以不残肢体和保存生命为限,从而正式且堂皇地开始了宗教裁判所用拉肢器和
红铁烙打击宗教异议分子的丑恶历史。一般认为,英诺诚四世的通谕是宗教裁
判所体系的最后定型;其中,肉刑的合法化与制度化又是关键的因素。
在此后的岁月里,梵蒂冈的精神统帅们也每每面对肉刑使用所带来的普遍
责难和批评;但是,他们显然从肉刑使用中尝到了甜头,尴尬自然难免,对异
端嫌犯摧残和折磨却一如既往,最多只不过假惺惺地强调了一下用刑的"公正"
和"温和"如只能用刑一次之类。这种强调的虚伪性实在不值得一评;所谓的
"温和"和"公正"是抽象而模糊的,宗教裁判员完全可以像揉面团那样随意
地变化出各类的形状:如果嫌烙铁和鞭子在嫌犯皮肤上留下的花纹不太雅观,
那么他们可以使用水刑,让慢慢地注入水牢的水漂白囚犯的身体总可谓温和了
吧;只用刑一次也行,他们可以将用刑分阶段地在一段时期里循序渐进地完成,
至于被告翻供,那就更有罪犯"重陷异端"的理由重新作业;不要遑论什么"仁
慈"和"公正",它的解释权就在宗教裁判所手上,罗素有句话可为注解即"宗
教裁判所的残酷有可能一度是出自有利于它的受刑人的考虑,因为有人认为尘
世间的短暂痛苦可以使灵魂免受永下地狱的劫难。但是,实用的考虑无疑常常
强化了审判官们的虔诚心愿……"(罗素,《西方的智慧》198 )。
当然,宗教裁判所的用刑也有其一定的程序;在我看来,这些程序再好不
过地说明了神圣法庭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虚伪。宗教法庭的目的在于让被
告屈服和忏悔--相比于不太识相的屈打成招者,天主教会更需要自觉自愿屈服
于其淫威的的可怜虫;所以,宗教裁判员在将异端嫌疑犯交给刑吏前是预先通
知被告的,"我们决定、宣布并决心在某日和某时对您用刑",并将各种刑具
及其功用如实介绍一下。这也许就是宗教裁判所所谓的仁慈和公正,也就是说,
如果其他方式如欺骗、恐吓与威逼能够奏效的话,宗教裁判员也舍不得随意地
撕去多年以来一直贴在正统教会脸上的那层仁慈。但是,假如异端嫌犯再不回
报宗教裁判所的这番苦心,或者他的回报没有达到宗教裁判员的期望值,那么
刑具的机械力量将毫不客气地关怀和照顾异端们的灵魂,虽然宗教裁判员那时
也依然能够和颜悦色--天主教的教士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堆出他们那种职业性的
笑容。
我们现在只能在一些古代图片里目睹宗教裁判所的拷问室了;即使这样,
它的阴森恐怖仍然可以控制和震撼我们的全部身心。在那里,地上摆设的是刑
具,墙上挂的是刑具,顶上吊下来还是刑具,烙铁在火炉里烧得红彤彤地,满
脸横肉的刑吏则杀气腾腾地持着鞭子。刑具形形色色,是特制的,有着其专门
的功能;固定受刑者有吊环和拷问架--它是诸般手枷和脚枷的组合,鞭挞用的
鞭子种类繁多,他们拶指或拶小腿骨的器具竟是铁制品宛如我们管子工的工具,
行刑凳倒既是戒具又是刑具--你可以联想一下中美合作所的老虎凳。有些刑具
的名称及功用也许已完全失考,但它们的奇形怪状仍足以引起人们最恐怖的想
象。宗教裁判所的拷问室还以使用拉肢器而著名;当拉肢器利用转轴五马分尸
般地拉扯受刑者的四肢时,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哀鸣声。
至于具体的用刑手法,刑具的繁多和复杂已经使我们的想象捉襟见肘了。
西班牙的史料显示,在那里,起码有三种肉刑因为不易落痕迹而程序化了。首
先是吊刑,扒光犯人衣服,双手反绑地吊在天花板上,然后突然松开绳子,让
犯人像皮球似地砸在石板地上。其次是水刑,犯人头低脚高地被固定在受刑凳
上,鼻孔和嘴塞满了亚麻布,刑吏将水不断地滴在布上以窒息犯人。第三种是
刑罚是用火的,在犯人的脚底上涂满油脂,将火移近,像烤乳猪那样文火炙烤。
够厉害的吧!这就是自由灵魂在中世纪必须面对的暴虐和残忍,它其实已经不
是我们的想象力所能穷极的了。
虽然宗教裁判所的肉刑制度一直是公开的秘密,但是,为了免受更多的责
难和维持虚伪的仁慈,正统教会仍然企图尽可能地捂住这个盖子。宗教裁判所
的工作人员必须发誓严守秘密,口供笔录也力求避免暴露刑讯逼供的痕迹——
刑讯结果要求被告一昼夜中"自愿"确认,审讯记录要特别注明它是被告在没
有压力情况下的自觉招供。因忏悔而获释的被告也必须发誓隐瞒神圣法庭的暴
力行为,否则将以异端累犯的罪名重新被捕,并必然在火刑柱上烧得灰飞烟灭。
医生始终是神圣法庭的重要配置,其作用是监控犯人的生理承受能力,并要为
受伤者治疗创伤;宗教裁判员认为这就是教会对异端仁慈的一部分,但它实际
上为的是异端能够活着而且似乎完好无损地被押上火刑柱。
这就是权力!这就是权力赤裸裸的自私和偏颇!我们可以看到,权力为了
自己的利益,是不惜奴役和殖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的;在中世纪异端裁判所治下,
宗教裁判员为了反异端可以利用一切社会关联,从而使仁慈、友谊、亲情、团
结之类价值因与控制和镇压活动的关联而丧失了其善的意义。我们也可以看到,
权力是耐不住寂寞的,宗教裁判所决不会让自己这台镇压机器因空转而损耗,
它因其镇压对象的存在而存在,没有异端它会制造异端;因此,它为了维持其
存在的意义必然走上反异端扩大化的道路,在这时,它是为权力而权力的,其
恐怖总是呈弥漫态势。
宗教裁判所的火刑
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是中世纪一个公众仪式,盛况空前;作为惩罚的公开展
示,它是一种"轰动艺术"(福柯语),基督教正统的精神霸权在这里完完全
全落实为对其属下肉体上的无限权力。
应该说,面对宗教裁判所如此的淫威和暴刑,任何对生命本身有所眷恋的
被告只能以屈服为上策。为此,他们还得终身承受佩戴耻辱标——一种十字交
叉的粗麻布条--或头戴小丑帽和身着魔鬼图案无袖衫即耻辱衣的侮辱,接受每
月一次或数次公开鞭挞的痛苦,煎熬披镣戴拷和难见终日的苦牢生涯,或者成
为奴隶在修道僧的皮鞭下苟且及在海船的浆手座上疲劳至死--将罪犯浆手锁死
在座位上是古罗马人的发明;即使从轻发落,日子也未必好过,没收财产是种
惯例——只有妻子的嫁奁才能例外,无休止甚至具有恶作剧嫌疑的忏悔、祈祷
和斋戒任务让受罚者的心灵至少在数年中不得安宁,额外的捐款和朝圣义务则
将不断耗费受害者可怜的生活积累以致于他们的后半生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
1564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教授维萨里因解剖尸体而为宗教裁判所判处死
刑,虽获得赦免,但仍被迫去圣地朝圣,结果这位近代解剖学的奠基人和七卷
本《人体结构》的伟大作者失踪于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之中。
但是,总是有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异端死硬分子,总是有屈服
过却一不小心又重陷所谓罪恶的异端累犯,总是有不肯归案而受到缺席审判的
异端逃犯;对于这些异端,宗教裁判所认为正统教会"仁慈"的劝导已无所作
为了,于是庄严地宣布将他们开除出教,并立刻"释放"他们。
千万别上当,在我们的字典里,从监狱中释放意味着宽容或宽恕,但宗教
裁判员当下的"释放"却没有增添这层意义,他们的"释放"意味的是抛弃和
放弃。正统教会自以为是上帝设在人间的办事机构,通往天堂的护照唯有它能
够签发;它的拒绝和抛弃也就意味着,天堂已向这些罪犯关上了大门,他们将
在火焚谷即地狱里永远遭受火焰的煎熬--《马可福音》说那里"必用火当盐腌
各人"。对异端犯最不利的还不在于此,福音书里说的火刑只是针对灵魂的,
但扯着上帝附体的正统教会却意犹未尽,为了普通教众的感性认识,宗教裁判
所难免不了以异端们的血肉之躯作一次的火焚谷的实景演示。顽固的异端是被
释放出了阴暗潮湿的监牢,他可以在中世纪的阳光底下温熙一下身子,但这是
他最后的享受,火刑柱已经矗立了起来,木柴和干枝堆积如山,他的肉体连带
其不屈的魂灵将马上在同样的阳光下为猩红的烈焰所吞噬。当然,具体作出火
刑判决的是世俗法庭而不是宗教裁判所,其意义却不过是刽子手在动刑前面戴
副手套而已。
由于王权和教权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许多世俗政权为了显示自己的独
立性曾经也抵制过宗教裁判所的血腥命令。但是,正统教会以其坚决的态度遏
制住了世俗政权的消极倾向;在1414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上,借批驳胡斯异端
的机会,天主教会索性将教会无权要求世俗政权处死异端的观点斥之为异端。
于是,命令世俗政权火焚异端,不仅是宗教裁判所镇压异端的基本手段,而且
成为正统教会控制世俗政权的一种手法。在王权获得宗教裁判所大力支持的地
区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王权和教权的合作是愉快的,异端的火刑率自然也呈
上升趋势。王权和教权的勾结始终是宗教裁判所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
我们在后面将提及的,它们之间力量的消长也决定了宗教裁判所的流变。
火刑的时间一般安排在节日之中,但这并不是定规。例如,在异端量特别
大的西班牙,火刑分大型和小型两种;大型的定在节假日、国王加冕或王子诞
生日--这需要积累一定量的异端死囚,小型的则随时随刻可以执行。死刑的执
行从来都有集体庆典的意味--在远古就是图腾仪式中的血祭,人类心灵的狂欢
在任何时候都带有他虐或自虐的因素;因此,在节日中安排火刑,我们除了推
测宗教裁判所为了展示力量的刻意外,也许还可以加上这一点文化学或人类学
的注脚。
由于火刑的判决和执行具有集体庆典的性质,各个牧区的神甫通常在一个
月前便开始通知全体教徒,邀请他们参加这一火的盛典,并许愿以一定量的赎
罪券;几乎没有人会拒绝邀请,好奇心人人都有,侥幸逃脱异端罪名本身又是
件可喜可贺的事,何况再加上赎罪券的诱惑和对成为异端同情犯的恐惧。在火
刑仪式的前一天,宣判的主席台在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搭了起来,而在临近的广
场上竖起了火刑柱——也有两者合在一个广场上的;火刑柱有直接竖在地面上
的,也有设在泥坛上的——如著名的贞德姑娘在受刑时便因泥坛和火刑柱格外
高大而未能让刑吏事先给她"恩典"一矛,周围则预先堆满了木柴。为了营造
气氛,宣判在许多地方通常要彩排一次,宗教裁判所成员和告密者则身着遮头
遮脸的白色长袍——可以联想一下美国"三K党"的服饰——与其支持者们在
城市的主要街道上游行。整个城市悬旗挂彩,整洁一新,洋溢着节日的喜气。
处刑当天的黎明,教堂敲响了召唤的钟声。囚犯们被押上了街头,游行的
队伍簇拥着他们;他们也被整饰一新,但赤着脚,脖子上套着绳索,捆住的双
手上灌满了绿色的蜡烛油--死囚在有些时候直接被套上了小丑帽和悔罪衣。押
解异端分子的任务仍然由宗教裁判所成员及其积极分子承担,他们举着白色的
十字架,宗教裁判所的旗帜飘扬在队伍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唱着教会的丧
歌,并不断奉劝异端们改邪归正。市民们则簇拥在马路的两旁,大声地辱骂着
异端,但抛掷石块受到教会的禁止。
在中心广场,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的头面人物已经各就各位,人山人海的
市民则热情地迎接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宣判仪式首先是作弥撒,接着一般是大
法官向国王宣誓坚持正统信仰和捍卫宗教裁判——例如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然
后是宗教裁判员冗长的布道。判决是宣判仪式的高潮,每一声判决都能引发阵
阵欢呼声——权力对捧场的欢呼声有着内在的需求;悔罪了的异端被迫当场穿
戴上了小丑帽和悔罪衣或者受到鞭挞,而火刑犯则被押到了火刑柱面前。
一般来说,死囚是站立着被铁链锁死在柱上的,也有让死囚坐在柴薪上的;
柴薪堆积如山,几乎没过蒙难者的头顶,围观者看清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就此而言,许多描绘火刑犯英勇不屈的绘画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为了防止
异端作最后的宣传,他的嘴里塞满破布之类的东西。在宗教裁判员及反异端积
极分子喋喋不休的劝说声中,刑吏点燃了火堆,熊熊的烈火迅速地吞灭了火刑
犯。添柴加火作为一种荣誉被授予对宗教裁判所作出贡献的人士或当地的社会
名流,据说,这能够增添他们的德行——宛如吃人血馒头可以治痨病一样。如
果说教会在这个时候还保留一点它理应拥有的仁慈的话,那就是它还能够要求
刑吏在死囚的脖子上挂上火药袋,在点火前勒死囚犯或者点火时用长矛刺穿犯
人的心脏;但以上手脚必须做得干净漂亮以免让群众发觉:教会重在炫耀权力
而非欣赏异端的肉体痛苦,但看热闹的群众则免不了要快感一把宛如当代人观
看暴力片那样。蒙难者的骨灰撒向河川或扬向天空,没有烧化的骨头需要重新
回炉加工以求彻底地销痕灭迹,旨在防止它们唤起人们对异端的回忆和崇拜。
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还经常用以追究和惩罚死去的异端,如英国神甫约翰·
威克里夫的遗骸在埋入坟墓三十一年后被判决送上火刑堆,连带受惩罚的还有
他的著述。焚烧异端著作也是火刑仪式的一大内容,《古兰经》、摩尼教经典
甚至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都享受过这种殊遇。另外,火刑还经常象征性地焚烧在
逃异端的模拟像;这一招我们是颇为熟悉的,因为它已为当代政治运动所继承
并有发扬光大的趋势。
从世界范围上考察,火刑倒并不为宗教裁判所专有,它是人类在蒙昧时代
处理巫师和邪术的普遍手段——北美的印第安人直至本世纪初还保留着以火刑
处理妖人的遗俗;火能够彻底销毁物质本体,古代人普遍信仰火的祛魔御鬼能
力。但是,宗教裁判所火刑制度并不能从这种普遍性获得多少辩护;没有一种
处刑方式像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对于异端者那样被滥用,它经历时间之长、波及
地域之广和蒙难者之多都是空前和绝后的。在宗教裁判所最为猖獗的西班牙,
火刑处罚发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1781年竟还执行了一例,而它的真正废除
要等到神圣法庭最终灭亡的1834年。
从语言的训斥到行动的限制再至剥夺生命的火刑,这就是罗马教会精神法
权在中世纪的具体的展开和落实:基督教正统是种权力,而权力将会依照自身
逻辑而无限制地扩张的。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宗教裁判所创立之初,
除了阿尔比战争期间外,天主教对火刑的使用还是慎重的,并没有如后来那样
肆无忌惮,只有当天主教精神霸权受到真正的挑战并真正丧失自信时,如在新
教革命时期和基督教正统在西班牙立足未稳的时候,火刑的使用才发展到令人
发指的地步。
如果还愿意为基督教正统思想开脱一下的话,我们现在最多也只能说一句:
当一种思想的存在和展示借助于法的力量时,它的行为准则已经同思想本身已
不相干了。